炭疽杆菌并未走远:从牲畜带来的传染病,到人类研究的生物武器
炭疽病的科学史
19 世纪中叶,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,牛羊养殖场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。当时的人们观察到,养殖场、毛纺厂、皮革厂的工人们常常会患上一种让皮肤溃烂变黑的怪病。由于剪羊毛的工人们患病率最高,所以也被称之为“毛工病”。

当时的很多医生都意识到,牛羊的毛皮与患病的工人之间,似乎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,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始终没有进展。
当时,人们相信一种叫做“自然发生论”的理论。这种理论认为,蚯蚓可以在土壤里产生,螨虫可以在灰尘里产生。其实现代人里也有人仍然相信,自己家的花是因为不通风而“生了虫子”。既然虫子都能自发地产生出来,那么医生们相信微生物能够在腐败的环境里自己长出来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“自然发生”理论最大的害处是,它成了人们探究微生物传播路径和来源的巨大阻力。既然微生物可以自己“生”出来,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什么传播问题了。
但是,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医生很反感这种说法,他并不相信微生物可以凭空地产生出来。这位德国医生,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现代细菌学之父——罗伯特·科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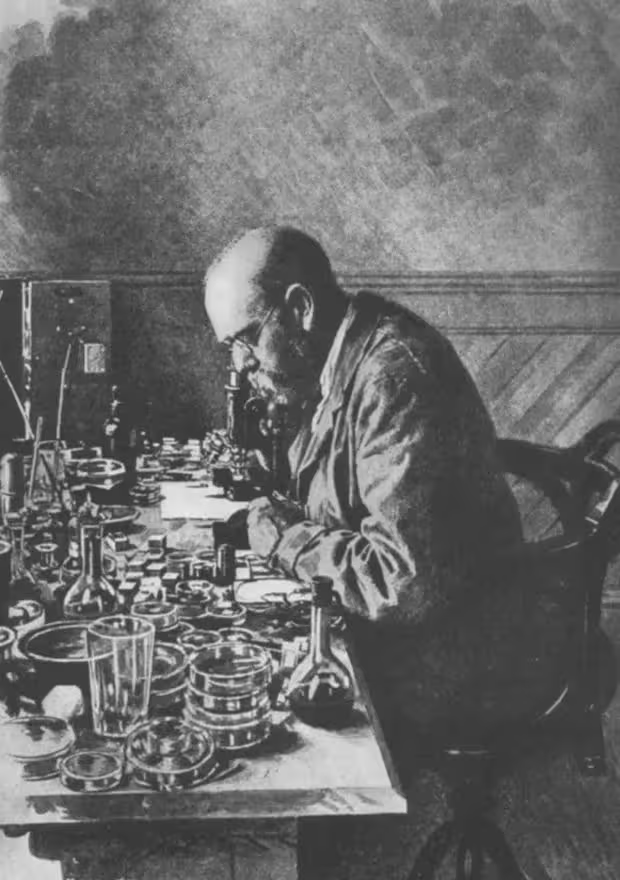
1876 年,科赫在患病牛羊和毛工病患者的皮肤组织中,找到了一种相同的杆状微生物,他把这些微生物叫做炭疽杆菌。他还用患病的牛的脾脏组织感染了老鼠,而死去的老鼠身上的组织,还能进一步感染健康的老鼠。这些实验让他相信,正是这种微生物,导致了牛羊和人的感染。
不过,科赫并没有满足于这些发现,他还想进一步搞清楚,这些炭疽杆菌是如何感染了牛羊,又是如何感染工人的。科赫暗暗决定,要在这项研究上走得更远。
在自然环境中,老鼠肯定不会用受伤的尾巴去触碰患病的牛的脾脏。想要找到炭疽杆菌的传播链条,就必须了解它们在离开生物体之后的生长和变化。为了做好这项研究,科赫在玻璃片上涂上各种炭疽杆菌可能“爱吃”的食物,然后把它们接种到玻璃片上,观察它们的生长繁殖。这个玻璃片,就是微生物研究的重要工具——培养皿——的原型。

科赫在培养炭疽杆菌的过程中意外发现,如果玻璃片上的培养基不适合炭疽杆菌的生存,它们就会形成一种椭圆形半透明的小体,这就是芽孢。科赫敏锐地觉察到,芽孢形态的炭疽杆菌与生长在生物体内的炭疽杆菌很不一样。
科赫通过切换不同的培养基和培养条件,尝试找到炭疽杆菌形成芽孢的条件。他发现,炭疽杆菌会用环境中的氧气是否充足来判断自身所处的环境。在富含氧气的环境里,炭疽杆菌就会在自身内部产生椭圆形的芽孢,外部的细胞组织也会形成一层坚硬的外壳,对芽孢进行保护。当芽孢重新进入缺氧的体内环境后,就会再发育成炭疽杆菌的形态,开始大肆繁殖。

简单地说就是,炭疽杆菌的状态负责繁殖,而炭疽芽孢的状态则负责感染。这些芽孢具有极强的存活能力。它们在羊皮上可以存活几年的时间,在直接的阳光暴晒下也能存活上百小时。在 150℃ 的干燥空气中,它们可以在一小时后仍然保持感染力。即便是在一些常见的消毒水中,它们也能存活几十分钟的时间。
了解了炭疽杆菌在两种状态下切换的机制后,科赫心中的谜团彻底解开了。炭疽杆菌的芽孢长期存在于土壤之中,污染草场。当牛羊吃了被污染的草,就会染病死亡,而患病牛羊的粪便和尸体则会进一步地污染土壤。牛羊在被污染的草场上活动时,草场上的芽孢会污染牛羊的皮毛,这就是剪羊毛的工人受到感染的原因所在。
比起科赫来说,他的老对手巴斯德在炭疽病的研究中显然更加务实。巴斯德有着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的双重身份。比起寻找事物的原理,他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。他首先告诫农民,应该用焚烧的方式处理患了炭疽病死去的牲畜,不要把死去的牲畜埋在土里。这个方法大大减轻了炭疽病的流行。随后,他又开始尝试制作炭疽疫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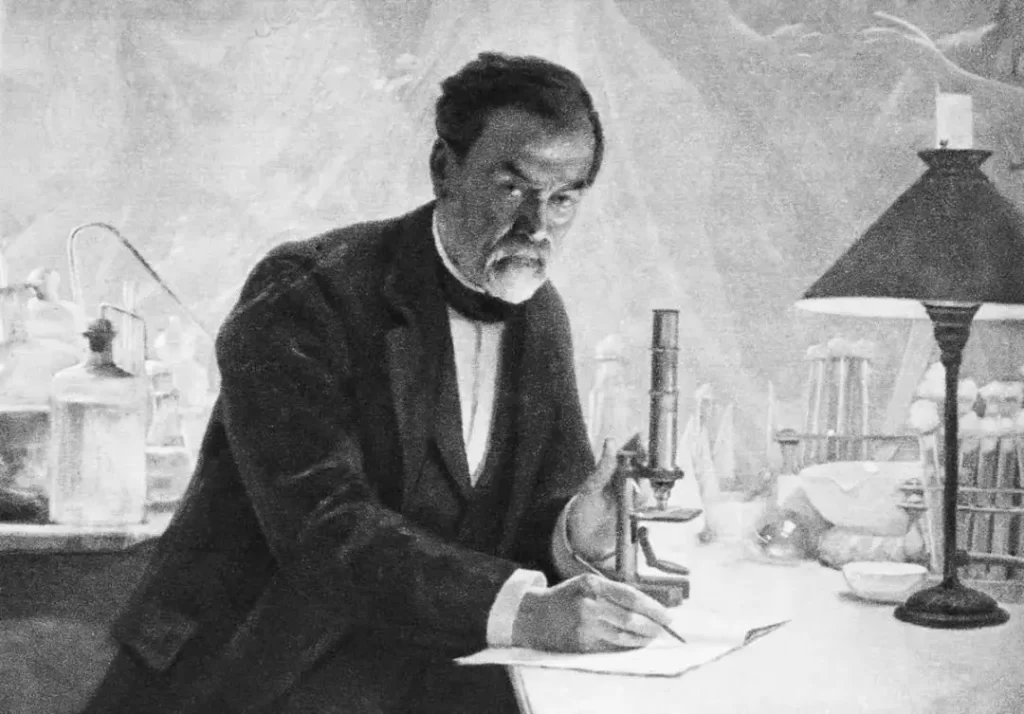
巴斯德选择的方向是制作减毒疫苗。1881 年,他发现在 42℃ 的温度下,炭疽杆菌似乎失去了发育成芽孢的能力。化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了巴斯德,他马上开始尝试在 42℃ 的富氧环境下用各种化学氧化剂来处理炭疽杆菌。然后用老鼠进行实验,看看它们的毒力有没有降低。
终于,在一次实验中,巴斯德观察到,用重铬酸钾处理过的炭疽杆菌不能够杀死老鼠了,而接种过的老鼠也不会再次被炭疽杆菌感染。巴斯德终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。
消息很快传到了巴黎一位有名的兽医罗欣约尔的耳朵里。罗欣约尔是一位坚定的疫苗否定者,他听说巴斯德在制作疫苗,觉得特别荒唐,于是向巴斯德发起了挑战:他出钱来购买实验用的绵羊,只要注射了疫苗的绵羊全部活下来,而没有注射疫苗的绵羊全部死掉,就算巴斯德获胜。
我们都知道,疫苗的保护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。要注射过疫苗的绵羊一只都不死,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。但是巴斯德知道,争论是毫无意义的,疫苗管不管用,应该用事实说话。虽然巴斯德并没有十分把握,但还是欣然应战了。
发表回复